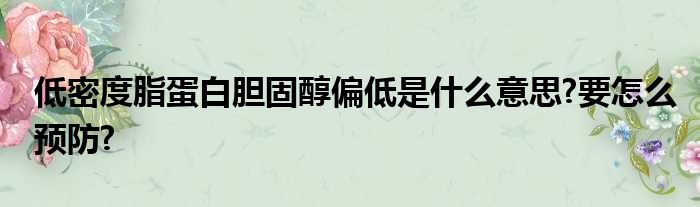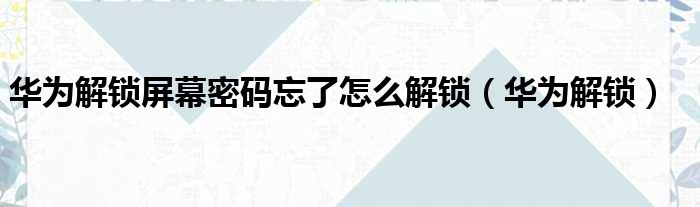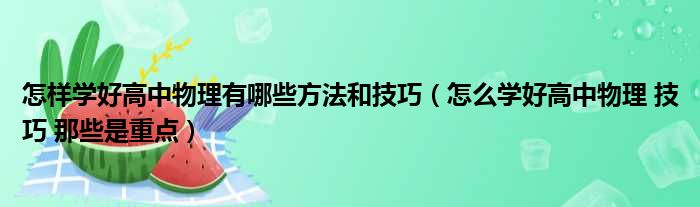今天为大家带来庆阳方言
嘎斯车把我们撂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的早胜原后,完成了它遣送我们回原籍的任务,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寺底大队第四小队的大场,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母亲虽然没有进过学堂,却深知读书的重要,一天都不能耽搁的。才过了两天,还没有彻底安顿好栖身之处,就催着蕞(sui)大带她和我们去学校转学报名,我上五年级,弟弟上二年级。
通往学校的路是蕞大用自己种的“捋捋(lue)扫帚子”扫开的(大竹子扫帚生产队才有),宽窄只能容得下一双棉窝窝(棉鞋)通过的路,如同一只蚯蚓在茫茫雪原上蜿蜒,离人家远一些的路成了众人老子———无人管,没有扫开。我们只好踩在别人走过的脚窝子上,高一脚低一脚,深一下浅一下跟在蕞大屁股后面依次前行。太阳出来了,足足有半尺厚的积雪反射着阳光,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这是农闲时候,加上大雪封门,空旷的原野寂静得只听见我们踩在雪上“喀吃,喀吃”的声音,人们都蜷缩在架板庄子或地坑院的窑洞里那热乎乎的炕上,光溜溜的席子上几双bie了裂子的脚,伸在用老布(一种自己织的布)缝下的薄枵的被儿里,外前人斜躺在炕上,头枕着炕棱边子抽烟睡觉,屋里人则赶紧打摭完锅碗瓢盆,奶娃的奶娃,做针线的做针线,有的用陀螺子捻线,有的砌鞋帮子或纳鞋底子,不让手闲。走了好一会儿了,我们连个人影都没有碰到,只有偶尔飞过头顶的麻雀和几声喜鹊或乌鸦的叫声,传达着莽原的生机。
走着走着,前面的端路子上出现了一个身影,只见蕞大大步迎上前去 :“五哥,这么冷,你还……”“没啥,日子泛长了,这活,天天是个天天”。蕞大的话还没有说完,对面就传来了这样的话语。抬头一看,站在面前的是一个比蕞大年龄大好多的老者 ,头上扣着一顶黑色的旧瓜皮帽子 ,上身黑棉袄上面套着一件蓝色老布大襟子棉领褂(马甲),后来才知道这种蓝是染坊特有的。老人腿上的棉裤面子依旧是老布的,而且是和蕞爷一样的大裆棉裤,裤腿用巴掌宽的两头留有穗子(流苏)的绑腿子绑着。脚踏一双在视频里看到的,只有有钱人才穿的那种前面有两条棱棱的棉鞋,显示着他昔日的尊贵。老人肩上一根磨的有些发亮的水担(扁担)上挂着两个不大不小的笼,前面的笼里有一坨干了的牛粪,后面的笼里则是一疙瘩狗屎。铁锨头插在笼里,锨把被筒着的双手抱在了怀里。白皙的脸上没有陇东人特有的“红二团”,稀疏发白的眉毛下面的眼睛虽然不大,却闪烁着睿智和仁惠,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般人不能企及的儒雅风范。“他老妈,这是五哥”,蕞大忙不迭地对母亲说。还没有等母亲开口,老人刚才那一脸的苦憷没有了,谦恭地冲母亲点点头:“哦,这是俊(zun)彦(父亲的小名子)家屋里和娃娃”。显然,老人已经知道我们是谁,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还有两个,大娃跟我生荣哥还在兰州,大女子到柔远城子哩”,蕞大说。姐姐在华池县山庄公社插队,华池有东华池和西华池之分,那时候,老上年人习惯把东华池叫柔远城子。老人把眉头一皱,有些生气地说:“qia(咱)的娃娃,跑到人家么远的地方zuo(咋)起lia?”蕞大说:“好哥哩,插队着哩,也是政策”。听到“政策”两个字,老人欲言又止,机警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抖动着山羊胡子,说:“哦,是政策,又是政策”。虽然我不明白“政策”是什么,但我从老人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丝凄楚与无奈。“娃,快叫五大”,蕞大催促着我们。“五……”,刚来老家没几天,我们还没有学会宁县话,开不了口。五大连忙说:“福祥,嫑梏娃娃了,城里nia叫爸哩,一时三刻娃娃还不习惯”,边说边用筒着的袖筒蹭拭了一下上嘴唇上的两绺子清鼻。
“噹——噹噹——”二郎爷庙座落的学校传来了清脆的钟声。“五哥,我给几个娃娃转学报名去了,你慢走,雪厚的也没有粪拾上,回去早些”,蕞大把五大肩膀上快要滑落的水担扶正,关切地叮嘱着,然后领着我们向钟声传来的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似乎自言自语,又好像对母亲说:“唉,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成了“分子”呢”?
“分子?妈,啥是分子?”幼稚的我听到蕞大的话,仰着头问母亲。母亲没好气地说:“啥是分子?分子就和你爸一样”。啊!顿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几个刻骨铭心的画面:凶神恶煞般的红袖章,一片狼藉的屋子,战战兢兢的母亲和呼啸着的那辆消防车以及父亲被人拳打脚踢,踉踉跄跄带走的背影……后来才知道父亲毫无根据的被诬陷为逃亡资本家和地主,因此抄家、揪斗、批判、关牛棚。我和母亲以及弟弟、妹妹也被遣送到祖籍早胜寺底。想到这些,吓的我打了个颤颤:难道五大和我爸一样,也被……
五年级教室在二郎爷庙里。一进门便是两根木棍支着的木头黑板,里面摆放着学生从自己家里端来的桌凳,大小不一,样式不同。斑驳的墙上彩色壁画依稀可辨。当秦校长把我领进教室时,十六个年龄比我大的男生齐刷刷抬起头来 ,诧异的目光齐聚在我身上,使我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女同学有十二分的不拘束(早胜话不拘束意为拘束)。“蛮子,你这有空位,让她坐你这”。那个叫“蛮子”的同学欢喜地挪出了压在屁股下面的长条凳子的一头,并用胳膊袖子擦了擦。我坐下瞥了一眼他的书,三个工整的毛笔字映入眼帘:秦成群。
一天早饭后,蛮子正教我写“大仿”(大楷),全校唯一的女教师牛老师进来说:“把凳子带上去大队开会”。蛮子也没有让我和他抬登子,扛上凳子走在后面,我则跟着牛老师走在最前面。所谓“大队”,就是一个四合头院子,上房比较高大,是大队部,门两侧分别挂着写有“中国共产党寺底大队党支部”和“宁县早胜公社寺底大队革命委员会”的牌子。两边的东西厢房是药房和小卖部。八个生产队除饲养员外的男女劳力都集中在这里,坐在马扎子或草墩子上,有的男人干脆圪蹴在房檐台子上。我们去时,三张桌子拼成的主席台空着,大队的脑系们还没有登台,院子里的空气也不那么紧张。女人们手里都忙活着,平时忙着一日三出勤,这可是她们做私活的绝佳时机。这不,有纳鞋底子的,有补补丁的,有给女子梳头辫帽辫子的,有让娃趴下捉衣服上虱子的,还有的干脆把衣服襟子一掀,娃躺在她的盘盘腿上吃奶,她则忙乎手里的针线。男人们抽烟的抽烟,谝传的谝传,年轻一些的目光在长的皙样的女人身上打转转。
“来了,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喧闹的会场顿时静了下来。中间留开的通道上,大队部的人依次走了过来,板着的脸就好像谁把他馍掰了。他们的屁股刚挨上凳子,就见支书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押上来!”这一声,把坐在最前面的不知谁家媳妇子怀里的娃吓得大哭起来,看到支书恼怒的面目,她也顾不了许多,当着千人百众的面,解开衣服,掏出白生生的奶头堵住了娃的嘴。回头一看,“分子”们被武装基干民兵押着进来了,两个民兵押一个胳膊在脊背后面的分子。刚走到人群中的通道,就听一个民兵吼道:“把你个坏㞞,还扭勾子(屁股)耍笑我哩!”说完,朝他押着的分子就是一脚。“唉,人家唱戏的旦角出身,就么一走木”。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悄悄地对另一个人说,言语里不无同情和怜悯。“哈哈哈哈……”人群中传来了笑声,一看,原来旦角分子禁不住民兵那狠狠的一脚,一头载在了前面分子的身上,这个分子腿有残疾,一条腿是个“硬腿子”,也倒在了地上。他可能问题严重些,被五花大绑着。倒地后怎么挣扎就是起不来。“笑你大个锤子哩,再笑,看我把你专政了”,支书声嘶力竭地吼道。一听“专政,人们一个个收敛了笑容,吐了吐舌头,再也没有出声,看着民兵把那两个倒地的分子架起来和其他分子一同押得在众人面前一字儿站开。在这些分子中,我看见了五大。
“今天,我们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是要对五类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支书的话刚一落地,心领神会的民兵连长使了个眼色,立即有民兵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对分子们“专政”开了。所谓“专政”,就是把分子五花大绑,再来个“喷气式”(绑在脊背后面的胳膊使劲往上搊)。分子们禁不住这一“专政”,有的尿在了裤子上,有的龇牙咧嘴,还有的圈在地上妈妈老子直叫唤。这一叫唤,把前面的那个娃娃吓得又哭开了。“把你个蕞先人有方子咧么?”支书怒目圆睁走过来,吓得年轻媳妇子抱上娃跑了出去。也许是年轻媳妇子走了气没出撒 ,支书瞥见了五队人群中五大的小儿子蕞贤 ,指着他吼道:“蕞贤,喊口号!”蕞贤哥立马站起来,胳膊向上一举:“打倒坏分子麻青连!”人们也举起胳膊跟着喊。“打倒………”“打倒……”分子们挨个被“打倒”着,当轮到五大时,蕞贤哥喊道:“打倒地主分子我大!”在场的人包括大队的脑系们都跟着喊:“打倒地主分子我大!”口号声响彻云霄。
目睹此情此景,母亲的话再次回响耳边:“啥叫分子?分子就和你爸一样”。我低下头擦了擦夺眶而出的眼泪,心里默默地祈祷:爸,你还好吗……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庆阳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