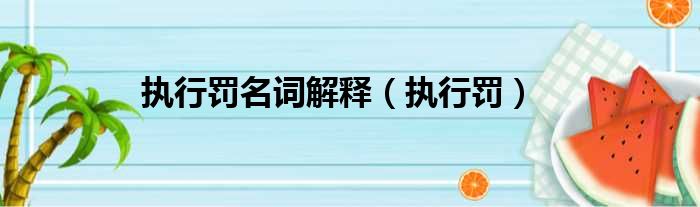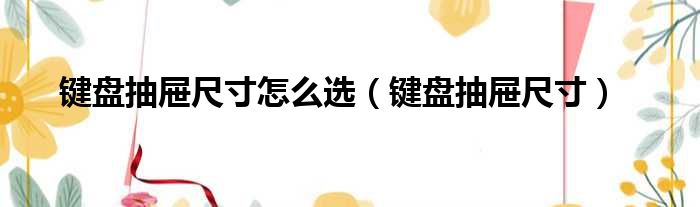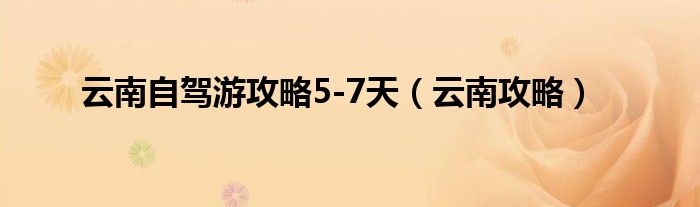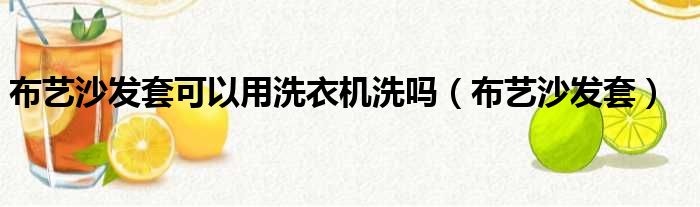今天为大家带来多想再回到老屋
在外地工作了十几年,搬过七八次家,回过千百次家。但不管我安家在哪,身居何处,总是忘不了家乡那栋老屋,总觉得只有走进那栋老屋才叫回家。
我的老屋坐落在湖南省桃江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是一栋三间房的红砖和泥砖混搭的小平房。她藏在一个三面环山的角落里,要靠到跟前才能发现,像一个害羞的姑娘。11岁时,我们全家搬到了镇上,就再也没有回去居住过。20岁以后,我北上东北求学,南下海南从军,再回家乡工作,一年难得回老家一趟。但不管我身在何方,老屋始终是我念想的伙伴,返航的坐标。
我出生时的老屋早在1987年就拆掉了,在原址上建了现在的房子。那时候爸爸在镇上教书,每个月工资只有45元。他省吃俭用,坚持每月存15元,攒了三年。再卖掉妈妈喂的两头大肥猪,才勉强凑齐了建房子的本钱。爸爸一介书生,却是什么都会。为了省钱,建材都是就地取材,自己烧砖,自己砍树,自己肩挑。从那时起,他就落下了腰痛的毛病,并困扰一生。
原先的老屋是用泥砖和木头搭建的。地面是凹凸不平的土面,桌子都立不稳,需要反复挪动才能找到合适的位置。房顶被烟熏得漆黑,常有蝙蝠藏在椽条的缝隙里。屋顶上漏下来的雨水,流过熏黑的瓦片和椽条,滴下来就成了酱红色,像牛尿一样。
客厅破旧的木窗下放着一张竹凉床,那是竹乡人家的标配,可以坐人,可以乘凉,还可以当床。下雨天,我总是站在竹凉床上,扶着两根被家里老黄狗咬烂的木窗栏,哼着《红灯记》里的京剧,望着对面郁郁葱葱的竹林。那里有妈妈经常带我光顾的菜地和一棵老梨树,梨子很酸涩,却是我年年期盼的美味。
夏夜里,流星划过明静的夜空,清风带着泥土的芬芳轻轻拂过,青蛙和蟋蟀合奏起田园小夜曲。萤火虫忽闪忽闪的,像坠落凡间的星星。爸爸把竹凉床搬到屋前的晒谷坪,一家人坐在上面乘凉。爸爸抽着旱烟,绘声绘色地讲孙悟空的故事;妈妈摇着一把烂蒲扇,时不时在我和哥哥身上拍几下。老屋抵挡了一天的烈日,也在享受那宁静与清凉。家的温馨,莫过于此。
老屋右侧是猪圈,里面养着一头小花母猪。花母猪喜欢晒太阳。农忙时节,猪圈外墙下堆满稻草。花母猪便悠闲地躺在稻草堆里沐浴阳光。每一次我都会躺在它旁边,轻轻抚摸它圆滚滚的大肚子,摸着摸着就会响起呼噜噜的鼾声。
老屋左侧是二伯家的房子,中间夹着一间杂屋。杂屋最里面是谷仓,两侧堆满了柴火、稻草和农具。那里是玩躲猫猫的绝佳场所,只要“敢霸蛮”,钻进稻草堆里,谁都找不到你。二伯是木匠,他用轴承和木棍做成贴地飞行三轮“滚珠车”,是我和堂弟最喜欢的玩具。老屋右侧有一个斜坡,是回家的必经之路。我们驾驶着“滚珠车”,从斜坡上猛冲下去,轴承里的钢珠哗哗作响,像坦克的履带驶过。但最后总要侧翻在坡下的草堆里才过瘾。
老屋后面是一个小山坡,长着许多杉树和竹子。老屋本生于后山,新建老屋的木材就是取自那里。平时需要竹子和木材,爸爸就去砍一根,越界的竹笋也会被父亲挖掉。妈妈把后山的干柴捡回家烧水煮饭,而我搜光了后山的果子。人、老屋和后山保持着一种共生关系。如今,人退山进,老屋终究还是把自己还给了后山。
和老屋一样,后山也承载了我童年美好的记忆。那时候的男孩子最崇拜战斗英雄。我捆上三根旧皮带,双手举起二伯做的木手枪,头戴竹枝编成的游击帽,左奔右突穿梭在林子里,一枪击毙一个鬼子。如今,三轮车和木手枪都已不知去向,二伯也已作古,只有老屋倔强挺立,后山依旧青葱。
1990年前后,农村还经常停电。家里常备了煤油灯和蜡烛。那时候,爸爸带着上中学的哥哥住在镇上的学校里,只有周末才回家。妈妈带我守着老屋。常常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后山的竹子在风中摇摆,沙沙作响。妖风穿过门缝冲进卧室,吹灭蜡烛,扬起蚊帐,令人毛骨悚然。妈妈害怕,她说我是家里的男子汉,能给她壮胆。
1992年我们搬到镇上后,爷爷奶奶在老屋住了几年。奶奶的70大寿还是在老屋里办的呢。那是老屋最辉煌的时候!四代同堂,子孙齐聚,热闹非凡。屋前的地坪里搭起了戏台,咿咿呀呀的花鼓戏从早上唱到晚上。鞭炮从村口就开始响起来,烟雾裹着老屋,随风飘进后山的竹林,宛如仙境。爷爷奶奶特地把头发染黑了,穿上新棉衣,端坐在客厅,接受儿孙们的叩拜。
未曾想到,奶奶在寿宴一个多月后便溘然长逝。那也是老屋最伤心的日子。寿宴的余温犹在,转眼就生死相离。爷爷没法一个人住在老屋,只好跟我们住到了镇上,老屋从此渐渐衰败。最初几年,多亏了二伯的照料,老屋还算健康。有漏雨的地方,二伯会爬上屋顶补一下。但毕竟常年无人居住,没有生气。横梁和椽条都老化得厉害,后来二伯也不敢上去了。
2001年4月,爷爷病重,临终前病体从镇上转移到了老屋。同样满身病痛的老屋等来了她阔别六年的老友。那时我还在县城备战高考。等我回到老屋时,爷爷已经离世。他像睡着了一样,安详地躺在我曾经和他一起睡过的床上,却听不见我深情的呼唤。
爷爷走了以后,老屋就开始急剧衰败。椽条断裂,瓦片掉落,最后墙体垮塌。只剩下红砖砌的前墙孤独却完整地挺立着,保持着她傲然存在的尊严,似乎在等着我回去。藤蔓趁机从后山侵占下来,铺满了卧室和客厅的地面,荒草从水泥地的缝隙里钻出来,宣告这片地方已成了它们的领地。
每次回老家,总是从村口就开始激动。路边也有一些像老屋一样老的老房子,都曾留下我童年的身影和足迹。它们与老屋一起,看我长大,送我离开,接我回来。其实老屋才34岁,真的不老,只是缺少关怀,才衰落至此。不是爸爸妈妈不回去住,而是因为生计和我们兄弟俩的学业才被迫离开。而我又在重复当年爸妈的抉择,为了生活和下一代而留在城市里。
老屋有生命,她只是不会说话。但她有她的表达方式。每次在老屋前驻足,她都会拉着我的手,邀我进屋看看。粗糙的墙壁轻轻抚摸着我的指尖,小声告诉我她的倔强与孤单。她饱经风雨沧桑,阅过世间生死。她感知人情冷暖,留下岁月痕迹。可看那美丽的红砖墙,和三十年前差不多呢!我知道,那是告诉我,她还年轻着,等着我回去陪她。但我不知如何应答。
多想再回到老屋,扒开灶孔里的热乎乎的草灰,翻出香喷喷的烧红薯,边啃边去对面的菜地里找妈妈。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多想再回到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