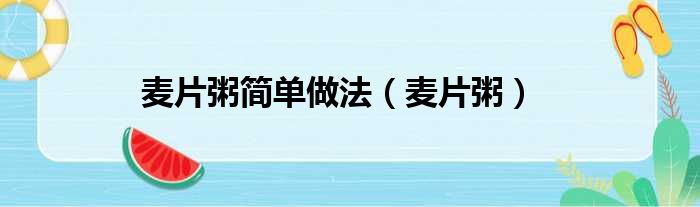今天为大家带来阴米粥
看到朋友圈的文友晒出一碗盛山阴米粥,融了蔗糖的黏稠红汤里,一粒粒软糯晶莹的阴米乳白乳白的,簇拥着一个圆溜溜的荷包蛋,其间还点缀了几颗鲜艳的枸杞,煞是诱人。我隔着屏幕,仿佛都闻到了软糯香甜的味道。

多么熟悉的阴米粥啊,这可是川渝一代的滋补佳品,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营养美食。可自从父母离世后,我很久没吃过阴米粥了,突然好想吃一口。
打开盛山植物园张总送给我的礼盒,牛皮纸精心包装的两小袋阴米跃然眼前,油亮亮的米粒一颗一颗,互不粘连,干净匀实,从纸袋的塑料膜窗口显露出来,看上去很有品质。于是倒出一小碗,我也煮起阴米粥来。
对照盒子上的说明书,我轻车熟路,将阴米简单地淘洗后倒进小锅里,加入清水、几粒大枣和枸杞,便生火了。阴米本是熟加工后晒干的食品,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大火烧开,小火慢煮,阴米在持续变热的水里一点点膨胀开来。待到米粒爆开变软,加入鸡蛋、蔗糖等配料,汤汁变得越来越黏稠,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阴米粥就出锅了。
甜香缭缭,舀一勺浓稠的粥送入口中,软糯的米粒已经软得不需咀嚼,从喉咙滑到食管,能感觉到一股暖融融的热流缓缓地流抵胃部。蔗糖特有的甜味顿时浸入五脏六腑似的,吃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吃完才抬起头。
从小到大吃惯的阴米粥味道,记忆中装满家的温馨和幸福。
看到盛山阴米制作的图作品中,叔叔阿姨在灶台忙碌的样子,也想起我的父母制作阴米的过程。
小时候,每到糯稻收获晒干后,父母就把稻谷分成两份,一份要留着做糍粑和汤圆,另一份就送到打米房变成糯米。几十斤糯米担回家,便开始做阴米。父亲清洗了那口年年都用的敞口瓦缸,傍晚时分将雪白的糯米一股脑儿地倒进去,然后加几桶清水把糯米全淹了,父亲还在缸口加了一个竹篾锅盖。一个晚上,米缸静静地立在一角,大家都不管它。
第二天早上,父亲用长长的勺子在缸里用力地上下搅拌,搅匀后,缸里的水染了米色,变得白汪汪的。父亲将它们一瓢一瓢地舀出来,然后换上干净的清水继续清洗。我经常巴在缸边看热闹,父亲是一边搅拌,一边捞起几颗米搁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捏来捏去,侧过脸对我说:“米粒变成肥嘟嘟的小胖子后就可以滤洗干净上锅了。”
母亲早已准备好几层的竹篾大蒸笼,在每格蒸笼底部铺上白白的纱布。灶台上一口大锅,加了半锅清水。灶堂里的火也生起来了,柴禾燃起的火苗在锅底吐着猩红的舌头。一格蒸笼平稳地搁在大锅上,父亲将泡好的糯米一瓢一瓢地舀进蒸格,用筷子均匀地推开,一笼蒸格就算备好。还有很多米,父亲就在刚才的蒸格上面加上新的蒸格,又重复刚才的事情。蒸格从底层开始垒放,根据糯米的多少选择几层蒸笼。
当所有的米粒都入笼后,盖上锅盖,就只管生火了。母亲往灶堂里塞大块的木柴,把火生得旺旺的。父亲拿来了几个小簸箕,用毛巾收拾得干干净净,放在一旁备用。
灶堂里的柴火熊熊燃烧,大锅里咕噜咕噜地响个不停,白白的热气跟着蒸笼攀爬,越升越高,越来越浓,一会儿的功夫,整个屋子里如同云雾缭绕。母亲望着高高的蒸笼,开心地擦着额头的汗珠,说:“上大气了,快了!“母亲往灶膛里送柴的频率慢下来,她说,只生小火能维持开水翻滚就行。
等啊等。母亲坐在灶台前汗流满面,一边生火一边关注着锅里的动静。父亲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准备着所有需要的东西。在我快等不及的时候,父亲搭了个凳子站上去,揭开锅盖,用筷子挑一团米粒开始察看。他把几粒结成团的米粒送进嘴里,上下牙轻轻地咂了几次,又闭上嘴回味了一会儿才说:“熟了,熟了!“母亲赶紧扑灭了灶堂的火,洗一把手,就和父亲一起忙起来。
父亲把蒸格一格一格地端下来,母亲接过来放到一边的案板上。簸箕就在旁边,父母牵着蒸格里的纱布,不用喊“一二三“,连纱带米,一下子就进了簸箕,干净利落。父母配合十分默契,所有的糯米很快都进了簸箕,蒸格里干干净净的。父亲母亲趁热将蒸成一个整块的米团掰成无数个小团,均匀地铺开,然后将簸箕端到通风口,等待晾干。
当米粒团晾到基本变硬时,母亲用小木锤轻轻敲打米团,一粒粒的米便脱离团队恢复了自由。此时的米粒仍保持着新米的模样,只是每一颗都变得晶莹而透明,看上去油亮亮的。阴米就这样诞生了。
父母将晾干的阴米送一部分给亲朋好友,其余的便用闭气的罐子储存起来,随吃随取,非常方便。
吃着父母做的阴米粥,我们几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后来,我们相继结婚成家,父母仍然每年坚持买糯米做阴米,给每个小家送一袋。再后来,父母老了,做不动了,老两口就到当地市场上去挑选优质阴米,继续给孩子们送。可去年,父母双双离世,我们就再没吃阴米粥了。
今天再次端起阴米粥,感慨万千。感谢盛山植物园的张总,成全了我问候内心深处的那份蚀骨亲情,成全了阴米粥给予我的那份浓烈的思念。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阴米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