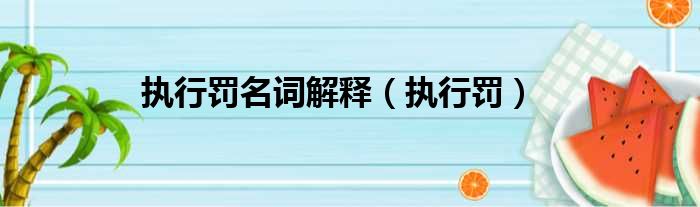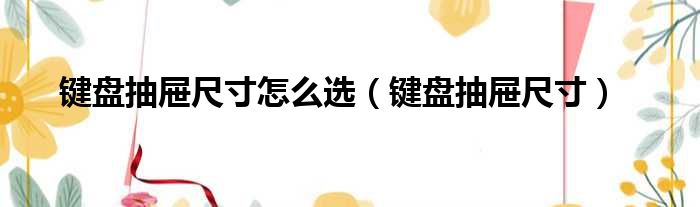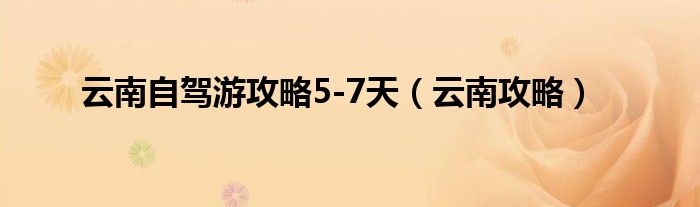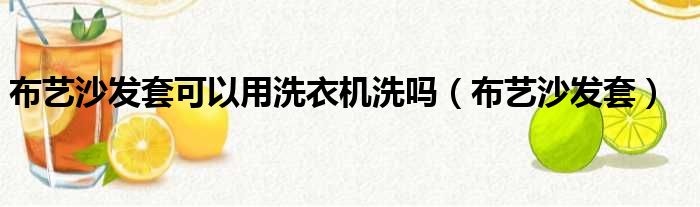今天为大家带来春韭与心香
一大早,从只留了一条缝隙的广泉小区东门侧身移步而出,一个人大踏步走入飞虹东街,车一辆接一辆泊在路旁,如一艘连着一艘的旱船。这样的春日,独自在空旷的北环街上闲晃是件很惬意的事,两行垂头散发的新柳,如烟的新绿,空气比平时清爽了许多。我时而信步,时而停下脚步尽情深呼吸。
想起昨晚接到母亲的电话时,我的确有些兴奋。自迁入广泉新居,母亲又执意同父亲返回老屋后,我似乎面临又一次精神断奶。“多多在,嫌多多,多不在,想多多。”每次在按下接听键前,我脑际总是一闪而过这样的念想。

电话那头,母亲带着新奇讲述关于瓦窑头的消息。语气中,我能清晰地想象出她表露于心的每一个细微表情。母亲已入古稀,我亦近天命,瓦窑头情结是我们母子之间最能点燃兴奋点的话题。尽管父亲对我们的滔滔不绝常常侧目,尽管瓦窑头至亲的人相继离世,但那份牵挂,母亲往往又寄托于周姓的后人以及曾经的左邻右舍。讣闻总是常常多于喜事,每每听闻,她总是哆嗦嘴唇,而后激动地红了眼圈。
谈及少时,鲜嫩的春韭刚上市,姥姥便在鸡窝边踮起小脚,掀开灰筛,伸手在母鸡身下的麦秸窝里探摸。没有收获期待时,她嘴里又忍不住抱怨“就知道吃”,我差点误解,直到她说出后半句“下个蛋能费死”,我才知道并非有意指责我。我对鸡蛋炒韭菜这道菜,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衷爱。“一股鸡粪气味,有什么好吃的”,我对姥姥作出这样宽慰的话嗤之以鼻。她常常把新收的鸡蛋,放在隐蔽的藏处,好不容易攒够了,又拿去看坐月子的远亲。我对那时的春天,充满期待,也常常等来遗憾。直到后来,我去一中读高中,开学时姥姥一下给我煮了十几个,我才知道,不坐月子也能这样吃。放进书包里的几个,后来虽然发了异味,我仍不舍得轻意弃掉,但长大的我,已从舌头上悟出了被呵护的暖意。
后来,得到姥姥的真传,母亲也会在春韭上市时,挑选红根的韭菜,为我做回面辣椒,点缀些鲜嫩的韭菜叶,撒些炒香碾碎的芝麻粒,握着雪白的馒头迫不及待地一蘸,陶醉地咀嚼着,吞咽着春天幸福的味道。我在眼角的余光中,发觉母亲长久地注视我的吃相,目光中荡漾着温暖与陶醉。
老舍先生曾说过“即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些孩子气。 ”那香味似乎诱着我,沿广胜寺熟悉的街道,迎着春日的晨风,向母亲所住的旧小区走去。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春韭与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