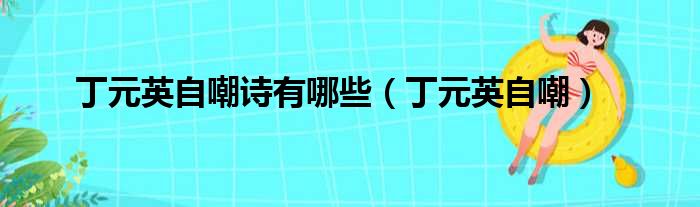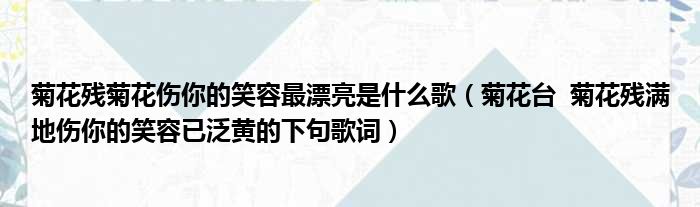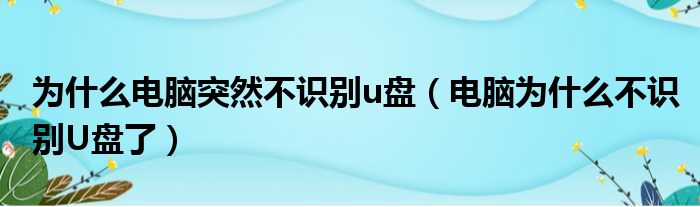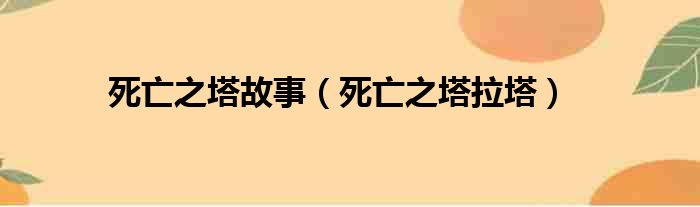这掐指一算距离中秋佳节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再要不了几天有十一长假了~~这几天还算是比较清凉,这小雨下的~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更新,这次为大伙儿带来了的是儿时记忆:忙年的内容作品、介绍以及图片之类,以下所要更新的文章内容很有可能甚是非常滴喜欢~原因则是会不时的会穿插各种图片,甚至于GIF动态图的展示,为了就是将文章女主展现于大家,让大家睡意全无!!!
儿时的过年,是清贫日子里的最大期盼,更是艰难中的温暖慰藉。
忙年,是湖南老家的方言,指的是为过年做相关准备的总称。一切与过年有关的衣食琐事,都随着年的临近而重要起来,各家的主妇也娴熟地按照日程进入到忙年的状态中。

忙年的重头戏从杀猪开始。最理想的是喂两头猪,那时候每家还有上交国家一头猪的任务,剩下的一头猪就是自家吃了。杀了猪的年才叫丰盛,否则怎么都称不上如意。
其实,从年初抓回小猪开始,极为精细与辛苦的喂养一直延续到年底。春夏季的猪草,秋冬季的红薯,不间断的米糠,一顿都不能马虎。我小时候最不乐意的事情就是割猪草,要仔细分辨哪些草不能吃,怕猪中毒,重重的一竹篓直将篾条勒进手臂上的皮肉,嵌成深深的几道槽。
家乡专事杀猪的屠夫有两个人,一队瘦脸的绍唐和四队方脸的绍安。
乡亲一致认为绍安杀猪的气势更胜。不管多大的猪,他紧咬腮帮,一双大手径直揪住耳朵,猪的一对前蹄完全腾空而顿时失去精神。更重要的是绍安每次绝对是一刀点心,粗壮的肘弯里猪脖子被完全扳直,刀尖对准位置,连刀把都全部捅入,随即一大股血顺着刀刃拔出来,然后被引到撒了盐的木盆里,一滴都不洒,极富观赏性。倒是听说绍唐有过几次失手补刀的事,被人忌讳来年不顺,东家都不乐意管饭。
猪的大小也是村里主妇们微妙的一次竞赛,小孩们跟着杀猪师傅走完一圈儿,每家猪的重量结果都出来了,于是各家主妇都有回话,“我都没怎么喂,这猪还争气。”“今年这猪不听话,那年我养的黑猪比哪家都大。”
猪被卸成大块摆在案板上,“抓回来时只有七斤,那次病差点死了。”“比去年还重十斤,没少淘力!”“几次切猪草都切到了手!”。。。女人总是絮叨着不容易。
接下来就是用粗盐腌起来,放进大缸里压实,更讲究的还伴腌了一只狗腿,据说风味更佳。半月后挑晴朗微风的天气晾晒,肉的颜色慢慢变化,看着都是殷实富足的喜悦。
忘了哪年邻近十队有家刚杀完猪,肉还是热的。主人家到屋后与人扯了一阵闲话,回来发现两箩筐几百斤肉全被偷光,一块不剩,差点儿直接跳了堰塘。那应该是天底下最缺德、最心狠的贼了,这是毁了人的辛劳,断了人的念想,灭了人的希望。
香肠、血肠、糯米肠都挂起来了,有心思的还把猪肝腌成腊货放灶上方燻着,那可是好的下酒菜。那年月这些东西都很金贵而稀罕,端上桌待客那是给足面子,一般的客腊肉就可以对付了。
有一次走亲戚,桌上一大碗香肠竟然堆着尖儿,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心情。却不想没吃几片就见了底,原来碗上搁了一个盘子平了碗口,不多的香肠就堆起来看着是一大碗。
做豆腐,是忙年的固定流程之一。新收的黄豆挑出颗颗饱满,泡了一天一夜,便用石磨磨成浆。推磨是个技术活儿,均匀的力度与转速需要灵巧的身手配合。我最喜欢干,当然是有酬劳的,等的就是一碗最为嫩滑的豆腐脑,这是豆腐压制之前只有老人才能享受的美食,拌入了白糖的香甜,长久回味在嘴边,直至今日。
留了过年的分量,剩下的就要做成豆腐乳了。干净温暖的稻草下面菌丝包裹着发酵好的豆腐,过了一遍白酒,均匀裹上辣椒面,放入腌菜坛中开始酝酿最正的风味。包括还有秋季的剁椒、雪里蕻腌菜、辣酱,这些都是上学的我们平常要带的菜,没有任何营养的咸口,不断催生出对过年无限的向往。
小时候没有什么零食,即使有也就是自产的如黄豆、豌豆、蚕豆这些“通气”的练牙齿的炒货,而真正代表着过年的高档次食品就是米花糖了。
早早地生好了半尺来高的麦芽,与大米或者红薯一起熬成粘稠的糖浆,混入炒制的焦香的糯米,放入方形的木制模具,用刀切成小片。还可以加入花生或者芝麻增加品种,味道比米花糖更香。有一年我和两个堂弟一起去姑妈家拜年,呆了半个月才回来。无比淘气的而我们把姑妈家里能吃的基本都消灭了,小孩一般高的坛子装米花糖,半个身子钻进去掏,最后把一点残渣都吃光了才回家。
小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到了那一天,过年的氛围才一天天开始浓厚,也是我“盼年”倒计时的起点。
腊月二十三,要送灶王爷的。灶神值班的地方在人间,他的主要职责是记录各家各户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在小年这天回天宫向玉皇汇报工作。我小时总纳闷咋没见他来过我家呢?不然我家的情况他没法汇报啊?如果汇报了那岂不是瞎编?看来灶王爷的工作也不是那么负责。
那天奶奶在灶头放了一个碗,萝卜上插了一柱香,对着已燻黑的灶神红纸条叩拜时,我把这个疑惑说了出来,头上随即挨了爷爷一烟袋锅,"你乱讲,灶王爷清楚得很呢,不高兴了就说我家不好,明年就没吃的了!"我顿时噤语,立刻恭敬起来。
有一年,小年已经过了,可我的新衣服还没看见,我急得每天缠着妈妈,抡起拳头转着圈打她。妈妈总说快了快了,早就把布送裁缝那里去了,师傅忙得很,明天去取。
一直到腊月二十九,我再也不相信她了,在家闹了一天,尤其是看到堂弟得意地显摆外地叔叔寄来的坦克皮帽子,我哭得呼天抢地。
妈妈下午出门去了,去了做裁缝的舅舅家。三十上午回来了,掂着一件深蓝色的长外套。估计舅舅怕我个子长得快,衣服得多穿几年,那件外套下摆快到了我的脚后跟,拖在地上走。
那个春节,我心满意足地拖着那件蓝色长衣飘过了很多地方。后来才知道,家里没有钱了,妈妈只好找舅舅凑了一块布,连夜赶制出了那件奇葩时装。
临近除夕的几天,忙年的节奏慢了下来,该准备的都差不多了。把地里的萝卜、白菜、蒜苗之类的挖回来,再上街去买回香烛、对联、鞭炮等。大人们对孩子的态度都好了许多,都因为是该过年了吧。
不过,还有一个词也和年相连,那就是“年关”。清账,都是大年三十为最后的关口,这才有了“有钱人过年,没钱人过关”说法。若有人催债上门,主妇倚着门抹着泪,男人一声接着一声的长叹,冲淡了所有的年味,透着无法排遣的无奈与辛酸。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儿时记忆:忙年